音乐付费制度的正当性本就无可置疑,过去数字音乐版权会增加成本,不符合互联网自由精神只是借口,对付费的抵制或恐惧会因交易双方的意思自治抵消,因为音乐平台与消费者关于是否付费或使用何种付费模式尚有商榷余地。付费制度在试图解决互联网产业和音乐产业的矛盾时,应避免牺牲用户的自主体验,否则将中道崩殂。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尚未流行。
继今年10月1日天天动听正式停止音乐播放服务后,阿里旗下的另一重要音乐载体阿里星球在上周二也发布公告,将在近期全面停止APP内的音乐服务。对此,除了转型为泛娱乐交互平台的推动力,在规范正版音乐压力下,阿里星球旗下虾米音乐和天天动听的严重盗版历史致使其曲库出现一定程度的匮乏,也被认为是其“退场”的拖拽力量。
音乐产品的版权认证和付费制度不仅仅让互联网音乐平台之间发生种种你来我往的厮杀,也让用户告别过去对任意作品唾手可得的习惯,而不得不同时装载多个APP,或在“走投无路”时购买数字音乐制品。
数字音乐平台的版权大战
实际上,在以国家版权局“网络音乐运营商应加强版权自律,尽快完成音乐版权的转授权谈判”要求为代表的各种政策背景下,互联网巨头们受制于过去盗版泛滥、资源共享的历史原罪,及迫切打造正版平台的公共形象诉求,早已在付费音乐的前提——正版音乐版权的争夺上打的水深火热。QQ音乐率先与7家唱片公司签约独家授权协议,百度与酷我也曾因争夺综艺节目的音乐版权闹得不可开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试图脱离以往的版权普通许可模式,纷纷在录音制品制作领域跑马圈地,相互指责对方盗用自身正版制品。
2015年5月下旬,阿里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称其260多首歌曲被酷狗盗播,而不到一个月,酷狗也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谴责阿里擅自传播其独家音乐。更早之前,网易云音乐就被酷狗起诉,因传播200余首音乐作品被索赔百万。网易亦称酷狗涉嫌侵权共37个案件,要求赔偿300万人民币。2015年年初发生的混战不止于此,腾讯起诉网易盗播,网易亦表示对方也曾未经许可传播200余首独家作品。这一系列互联网音乐平台之间的“互撕”最终以微信封杀网易云音乐、阿里系天天动听而达到高潮。
以往音乐作品版权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初期被牺牲,各种播放器在录音制品著作权领域“裸奔”,以侵权行为换发展空间的路径被证伪,而版权争夺战之后的音乐付费趋势将正当化。用户在企业跟进后也被动的加入正版保护的道路。
但数字音乐播放器很难垄断所有版权,用户为某一作品同时使用数种同类产品的体验也相对糟糕,一轮版权厮杀后,巨头们也开始版权合作之路,腾讯和网易就在前述法律争端后达成版权共享协议,而支持这种模式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数字音乐平台和唱片公司的独家授权协议通常时间较短,一两年过后,就会面临新一轮的比价,因版权的高流动性而丧失用户黏性想必得不偿失。二是花费巨资囤积版权,必然面对消化资金,实现版权红利变现的压力,除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付费通道,版权分销亦成为个别坐拥大量录音制品著作权播放器的当然选择。
美国与欧洲的著作权扩张案例
著作权人的主动维权和公开发声行动都是遏制侵权蔓延,甚至拓展权利边界的尝试,将之纳入司法范畴后,法律认可所发出的指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判决,也可能是盗版猖獗的罪魁祸首之一。2006年的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即是后者,当时,以索尼、华纳为首的七大唱片公司发起联合诉讼,称百度的MP3搜索下载服务侵犯其专有著作权,百度则辩驳,侵权的是提供盗版资源下载的网站,而非搜索公司。最终法院也判决认可百度向网民提供的是搜索引擎服务而非侵权MP3音乐作品。
与之截然相反,发生在上世纪末的数起美国式数字音乐服务的责任分配争议,则同样验证了司法裁判和商业模式之间犬牙交错的利益争执。由于Napster可以将“音乐作品从CD转化成MP3的格式,并提供平台供用户上传、检索和下载作品”,曾经由录音制品制作者掌握的传播渠道遭到碾压,用户利用互联网可以肆无忌惮的直接或间接传输音乐作品。诸多音乐著作权人在发起史上首次针对最终私人消费者的大规模诉讼后,将矛头指向网络服务提供商,而法院一审和二审都判决Napster败诉,称其必须承担帮助侵权或替代责任。随后,第二代音乐共享软件改变技术设置,脱离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控制,试图从主观无过错来合理规避了原判决的侵权要件标准。对此,美国最高法院在新的判例中提出新型独立的引诱侵权概念,认定“如果当事人散布设备的行为具有推广该设备侵犯版权利用的目的,例如通过明确表示或者其他积极步骤助长侵权,即应该对第三方因此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在这期间,某在线音乐商店虽致力于推进收费下载,但由于其坚持不使用任何阻止用户的技术,和著作权人希望借技术手段控制传播范围的目标冲突,最终难以与Napster抗衡。而苹果公司因其提供的录音制品的格式与当时的MP3播放设备不兼容,打消了著作权人对非法传播的疑虑,因此iTunes获得了作品授权。
伴随技术进步,不断出现新的传播方式,而著作权人出于固守原有权利许可模式,倾向控制传播渠道来保证自身利益,因此新技术诞生风靡常与之发生利益龃龉。例如,美国最初的著作权法颁布之时,音乐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只包括复制发行,而没有对公开表演做出规定。100多年后,才将“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表演”纳入权利体系,但实践中“营利性质”认定困难,立法者也认为公开表演有助于复制发行权利最大化,这使实际侵权成为常态。为克服取证复杂、利益分散、维权成本高昂等阻碍,“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者协会”得以成立,通过其努力,不仅司法判决认定餐厅酒吧等机构需在演奏音乐作品时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立法也让广播组织为其广播音乐作品的行为支出费用。
从美国音乐作品著作财产权边界的扩张历史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免费之路必然会有尽头,著作权人积极运用既有法律条款或通过诉讼推动判例的维权模式值得借鉴,从“以用设权”的立法路径,即随着音乐作品从复制发行乐谱到公开表演,再到广播和网络传播的权利内容的叠加法中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免费之路必然会有尽头,二是但是立法者应防止在权利许可过程中,著作权人对新传播手段的保守态度导致部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为垄断实体,继而阻碍音乐作品的传播效率,影响“物尽其用”。今年11月,德国音乐版权机构GEMA与YouTube持续数年的版权诉讼终于落下帷幕,GEMA原诉求每首歌每播放一次即支付0.375欧分的补偿标准,但最终双方同意放弃所有尚未解决的诉讼选择和解。考虑到在案件发生之时,欧盟正尝试修改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方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更多的控制权,YouTube此时的和解也算是明智之举。
欧洲最流行的法国音乐流媒体服务商Deezer就曾透露,向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移转的内容成本占据了公司营收的四分之三,苹果公司的工作人员在2015年就表示“Apple Music在美国71.5%的营收将被支付给商标、曲作家、艺术家以及其他合法持有者。而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该数字还会上升至73%之多。”但公司经营成本的上升并不等于著作权人最终收入水平的提升,今年,美国版权委员会就针对音乐流媒体发布了再次提高的广播和网络传播税率,其中,免费音乐的新税率提升20%,至每首歌0.0017美元,但由于付费无广告音乐的税率下降,税率平均提高了15%。
但正如立法需对流动的权利平衡进行谨慎考量,防止一方坐大,著作权人并非永远扮演着受害者角色。法定使用和合理使用就是对著作权侵权现象的豁免。例如,2014年时英国就规定,用户出于私人使用的目的,拷贝自己拥有的音乐、视频、电子书、CD和DVD或转换数字其格式的行为不属于侵犯著作权人复制发行权的范畴,这一“私人复制豁免”条款顿时引发轩然大波,结果今年年中,该条例即被撤销。虽然该条款未能成行,但其设定之初也蕴含了权利用尽原则,即防止著作权人无限扩张其自身权利,并可能多重获利。
著作权“去产权化”被否定,集中许可补充法定许可
过去的唱片公司和广播电台既是占据大量著作权的内容制造者,也具备控制传播渠道的身份,他们的经济利益来源于音乐载体的贩卖或传播权利的许可,因而他们更倾向于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当作一个新型但又传统的分销商,并对其侵蚀产业份额生出警惕。对传统音乐产业的主体而言通过作品获取版权收益的典型思维天然的指向了付费音乐,这与“草莽时期”比拼流量的互联网免费自由的大旗天然不容: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初期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通过搭建平台和免费音乐吸引流量,进而向第三方获取收益。
当然,已经流行的免费通道并不能以习惯为由自动合法化这种忽视产权保护的商业行为,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终端消费者与提供盗版作品的互联网提供商都曾剥削了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而平台因流量获得的种种收益只不过来自于著作权人应得经济利益的让渡。
虽然互联网经济中存在自愿“去产权”的公共许可。比如,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各种网络百科应用,构建于用户自发生成内容并传播的基础上,免费的一大激励来自于已经公共化的产权。但音乐作品想必很难移植此种乌托邦模式,一是录音制品的著作权人通过授权许可获益的手段虽经历技术变迁,但其价值取向未曾消亡。二是目前部分仍旧存在的免费且合法的数字音乐,受制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与著作权人不对等的协商地位现状,而非后者的心甘情愿。
但增加获取版权难度的除了著作权人个体数量的庞大,另一难点在于著作财产权种类的复杂无形间增加了授权成本。也正是因此,有业内人士呼吁将复制、发行、出租、广播、网络传播等权利统一为“商业使用权”,再让录音制品制作者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通过合同协商分割“子权利”。但反对声也相当激烈,认为此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将得不偿失,表示权利的合并会使得原有权利独立性丧失,且借助合同分割的“子权利”因缺乏绝对性和排他性,更易滋生不必要的纠纷,并由此降低传播效率,与降低交易成本的初衷背道而驰。不过,一站式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解决权利类型和归属分散的弊端,我国著作权法在修改时就曾因是否保留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发生过争议,而最终,社会选择鼓励著作权人通过集体管理组织代表,一次性打包授权各种财产权。这种集中许可的优势在于避免了法定许可导致的著作权人的许可权被剥夺,定价权转移至行政部门,诱发权力寻租的不正当现象,可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调整费用标准,遵循市场规律,既方便了终端用户对音乐作品的合规获取,也给予著作权人足够合理的经济诱因。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向录音制品制作者或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支付版权费用还只是音乐付费制度的上游,与录音制品制作者类似,互联网公司将不单单是付费主体,也将成为面向下游用户的收费对象。但对于消费者而言,付费音乐并不一定导致用户需为每首音乐作品支付相应价款,平台既可以选择向第三方收取广告费用,免除因收费驱离用户的尴尬处境,也可以在向终端用户收费时依据频次、数量,包年包月等划分费用阶梯。
尽管音乐版权大战让产品价格水涨船高,也有人表示:“音乐版权对于数字音乐行业的影响力,与视频版权对于在线视频行业的影响力,处于同一量级。”但后者传导到上游的高片酬等现象并未复制到歌曲制作者身上。我们反而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关于大陆音乐行业不景气的抱怨,对音乐作品的侵权行为依然俯拾皆是,大众在多年免费获取音乐作品的消费习惯下,不仅对以付费为主的正版转型模式尚存抵触和侥幸心理,更对众多维权行动不够理解或认同。由刘欢、谷建芬、三宝等数十名音乐人组成的著作权代理机构——华乐成盟,向《中国好声音》发起数起跟公开表演权有关的诉讼,起诉格力电器等侵权主体因“董明珠自媒体”以广告用途未经许可侵权使用歌曲《因为爱情》,都只是在舆论略微掀起一些波澜。
创作人难以从作品的版权收益中获益,自然使得原创者的生产环境相对恶化,原创音乐的品质和数量也就相应下滑。这也难怪不少自诩歌手的演艺人员常常“卖惨”,控诉版权利益分配的不公。黄子韬在本月初的一次颁奖礼上,再一次重复了很多歌手都曾表达的意念,即多数人都认为中国音乐市场目前没钱赚,他做综艺拍电影都是为了有机会去做音乐,而音乐才是他“最重要的梦想和人生”。“打广告、卖衣服、开饭店都是为做音乐积累资金”的薛之谦也曾透露,其歌曲《演员》的点击率已经破亿,但其个人并未从中获得一分一毫的收入。
结语
总之,音乐付费制度的正当性本就无可置疑,过去数字音乐版权会增加成本,不符合互联网自由精神只是借口,对付费的抵制或恐惧会因交易双方的意思自治抵消,因为音乐平台与消费者关于是否付费或使用何种付费模式尚有商榷余地。付费制度在试图解决互联网产业和音乐产业的矛盾时,应避免牺牲用户的自主体验,否则将中道崩殂。
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逐渐摒弃行政门槛,维权行动日渐高涨,实体唱片向数字唱片转型以及政策合规压力下,著作权人略有上升的谈判地位和大众对知识产权领域价值位阶的崭新认知,都将有助于互联网巨头消化因收费流失用户的忧虑,并在抢滩正版版权后,加速推进付费音乐。
“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尚未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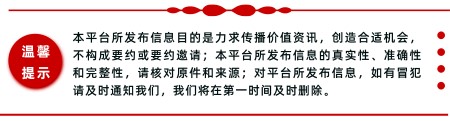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